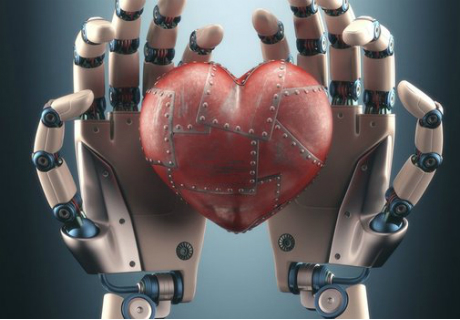韜光養晦
中共十九大以來,大家都應該經常聽見「毛澤東讓中國站起來,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習近平讓中國强起來」這口號,意味着中國進入新時代,甚至正式向以往韜光養晦的時代告別。儘管十九大以後,中國的確勢頭大好,外界亦開始認真看待中國的優勢與強大,可是自從2018年特朗普向中國叫板,中美瀕臨爆發貿易戰,中國電信設備商中興通訊面臨美國禁制,就連紀錄電影《厲害了,我的國》也匆忙下架,則令人不禁反思中國近年是否鋒芒太露,是否過早脫離「韜光養晦」這戰略方針。
(網上圖片)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鄧小平就國際形勢驟變的情況,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對、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些重大指導方針,最後用「韜光養晦」高度概括了新形勢下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
「韜光養晦」雖不是出自道家人物口中,但其收斂光芒、積蓄力量的意思卻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味道。事實上,我國史上的漢唐盛世很大程度也是「韜光養晦」的直接結果:漢高祖劉邦於西漢初年遭逢白登之圍 ,幾經辛苦才從匈奴包圍中脫險,自此便一直採取朝貢和和親政策,韜光養晦,最後待至漢武帝時期才得以一雪前恥、收復失地。唐代伊始唐高祖也須對突厥稱臣,唐太宗亦經歷了渭水之辱,幸好唐太宗勵精圖治,派李靖率大軍平定東突厥和吐谷渾,成就了隋唐盛世。筆者相信鄧小平也是根據這些歷史事實來制訂其「韜光養晦」戰略方針,令中國得以從極其困難的境地中走出來。
之不過,一直以來作為中國的假想敵的美國,可不是匈奴突厥之流,而是當世獨大的超級大國。誠然,中國享受了20至30年的戰略機遇期,國家實力大幅增加,然而這卻是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未能分身對付中國,
(網上圖片)
同時又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國力大損、神話破滅的結果,可是這卻使中國產生了過度樂觀甚至輕敵的心態,加上習近平已大權在握,眾人一面倒歌功頌德,令中國不得不提早放棄「韜光養晦」方針,造成目前鋒芒畢露、過早亮劍的情況,招致美國出手反擊。
(網上圖片)
很多人都誤解了「韜光養晦」代表銷聲匿跡、無所作為,這是不了解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結果。事實上,「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係─沒有「韜光養晦」的前提與指導,「有所作為」也很容易會走樣變形,因此國家越強,才得見「韜光養晦」的可貴。所以美國一本專著的書名說得很對:那是《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中國只要繼續韜光養晦,那麼要在2049年,即中國建國一百年之前,取代美國,稱霸全世界,並非夢想;然而過早出頭,頭腦發熱,則會丟失難得的不敗之地,招致眾強的圍攻,得不償失。
如今之計,中國應該盡量促使美國驕傲自大,使它更肆意去濫用其霸權,盟友及支持者離心離德,以自己的盲動來終結其霸權─這也是道家戰略的精髓。
撰文:袁彌昌博士
政黨政策總裁及大學講師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碩士,香港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現爲政黨政策總裁,並於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
May 31,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