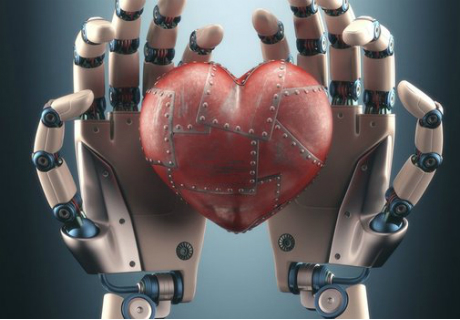亞洲新科技及青年的影響力
上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即ICRC)的主席彼得 毛雷爾應香港科技大學的新任校長史維教授的邀請,來臨香港做第一次的公開論壇。這次論壇有多達400人參與,當中兩位領袖的交流刺激,讓會場氣氛濃厚。對談中的一些觀點很值得記錄及讓大家思考,故我再借此平台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主題演講的部分,毛雷爾主席指出,在全球衝突地方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國際機構難以再依賴傳統的捐款或慈善的經濟模型經營下去。故此,他主動邀請正如日方中的亞洲科技企業一同合作,利用新科技及創新合作,為戰區找出共贏的援助方案。在其後的問答環節,有與會者回應此觀點問,亞洲的科技企業甚至政府有其新的力量,但他們的角色是什麽呢?毛雷爾直接支出,當前國際的多邊援助項目裏面,以歐美的援助為主,當然國際社會希望見到亞洲社會能在國際舞台有更大的擔當和角色,這個ICRC是積極推動及鼓勵。
(網上圖片)
接著,有一個工程系的同學提問,他們不斷研究新產品,我們怎麼能阻止他們研究出來的創新技術不會被利用到害人的地方呢?這是一個多麼赤子的提問,讓全場鼓掌。毛雷爾主席毫不遲疑回應,他說:「工程技術來自研究員,但技術的利用,從來都不在學術研究員的手裏,反而它從來都是被政治家來決定。故此,大學及國際機構需要攜手爭取政治的engagement渠道。」這個簡單但坦誠的回應,再次惹來全場的掌聲。
(網上圖片)
在散場前,有人問史維校長,既然國際機構中亞洲人(甚至香港人)的代表性那麽低,身為科大的校長,他有什麼計劃推動更多亞洲人預備一個國際機構的事業呢?校長精點回應,科大這次誠邀國際組織的主席來港對談,就不是正正讓大家,甚至他自己以科研為主的學生體驗到,真正的國際外交人員的經驗是如何累積回來的嗎?而科大也會積極推動更多與國際組織的合作機會,讓在港研讀的年青人有機會在國際外交市場競爭。
確實,科技的進步及國際環境的嚴峻讓國際機構和大學都要求變,而促成這次合作。每年在香港有數千場標榜著「國際性」會議,當中以經貿為主。但真的能把地緣政治及外交手腕等視野直接帶給年輕的,真的不是很多。這次香港科技大學踏出的第一部,除了為自己的學生帶來刺激外,希望也為一帶香港人拓寬更大的人生視野。
撰文:葉維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外代表
Jason早期任職投資銀行。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進修國際關係,獲推薦兼讀聯合國大學。其後,加入瑞士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從事人道外交工作。曾被派駐巴勒斯坦,阿富汗等戰區,經常與非政府軍事組織接觸,處理戰事民生問題。
November 23, 2018